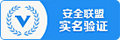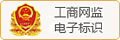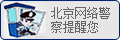"不求同生,但愿共死"的愛情也是咱們所向往的另一種美好,近日,在晉江安海鎮(zhèn)下山后村,一對83歲老夫妻一起出殯,這兩位老人感動了村里上百數(shù)人自覺的前來為老人送別。
6 月13日晚上,吃了一小碗飯后,陳淑榮和黃淑霞兩人早早睡了。直到深夜時分,見老伴難過、掙扎,黃淑霞當(dāng)即起身,來回輕撫著老伴的腹部,后代們也急得在床前圍了一圈。次日清晨4點多,陳淑榮閉上了雙眼,后代們號啕大哭,黃淑霞則靜靜坐在床邊發(fā)愣。后代們其時憂慮,她是悲傷過度。誰也沒有想到,為老伴穿好壽衣后,黃淑霞突然喘粗氣,接著安定離世。時刻定格在清晨6點,天已大亮。
長孫陳長賢說,之前有悄然聽到爺爺奶奶的對話,爺爺說““能夠活不了多久了”,奶奶接了一句:“你走,我也走,同生同死”,其時驚奇之余更多的是感動,”“也罷,結(jié)伴去天堂,有伴,不孑立。”
陳長賢說,上一年年初,爺爺查出沉痾,到醫(yī)院住了兩個月,雖然后代都輪番照看,但奶奶仍要每天守在爺爺床前,形影不離,我們憂慮她身體吃不消,但誰勸都沒用。“連醫(yī)護人員看到,都覺得這對白叟風(fēng)趣、感動。喂飯、喂藥、蓋被、穿衣、拉家常……奶奶都要親自來”。
后來,每有親屬來醫(yī)院看望陳淑榮,在一旁的黃淑霞,就像平時惡作劇相同,說“他走,我也走”,我們都笑笑罷了,誰也沒確實。
本來他們的愛情沒有他人幻想的那樣轟轟烈烈,66年前在那個時代,婚姻都是媒婆牽線、家長包辦,陳淑榮和黃淑霞也不破例。黃淑霞就在近鄰菌柄村,但直到成婚當(dāng)天,陳淑榮才見到他的新娘,兩人同歲,他大她三個月。婚后日子也很一般,他吃完飯就往生產(chǎn)隊跑,興修水利,上山勞作,她則首要忙里忙外,照料家務(wù)。在后代看來,他們的愛情沒有他人幻想那樣轟轟烈烈,每天都差不多,起床、吃飯、干農(nóng)活、睡覺,乃至有點平平庸俗。
“僅有雷打不動的是,差不多每天清早五六點,奶奶都要起床煮米粥,飄出香味后,才叫爺爺起床。”已為人父的陳長賢說,在他的回憶中,還未見過爺爺奶奶拌嘴或打架,而形象最深的是,爺爺奶奶很愛談天。
“小時候放學(xué)后,將書包扔在家里,出門玩之前,看到爺爺奶奶坐在門口椅子上談天,我玩夠回來,他們還在聊,仿佛總有聊不完的話。“聊的都是家長里短,要么聊3個兒子1個女兒5個孫子,要么聊打農(nóng)藥上肥收割……掰著手指翻來覆去地算,聽得旁人都快睡著了,但他倆仍是聊得津津樂道。”
6月18日,村白叟會出納陳長純,接過一包沉甸甸的紙幣,疊得整整齊齊,用報紙包著,有各種面值,最大的100元,最小的5元,總額1萬元。本來,這筆錢是陳淑榮臨終前,告知后代代捐的。陳長賢說,“這是爺爺臨終前一再告知的僅有一件事,爺爺其時說,‘我還有一萬塊錢,你們幫我捐給白叟會,就當(dāng)最終一次交會費’”。
“這些錢無非是后代給的零花錢、壓歲錢,爺爺奶奶從牙縫里攢下來的,要攢這么多,得多少年啊!”
在村白叟會副會長陳長標(biāo)眼里,陳淑榮和黃淑霞熱心公益,“20多年前,有高中文化的陳淑榮當(dāng)過村白叟會首屆常務(wù)理事,自覺掌管廟會活動還兼職當(dāng)義工”。這些年,陳淑榮和黃淑霞在村里積累下好口碑,昨日又是兩人一起出殯,村里有五六百名村民自覺相送。就在送葬部隊延伸村道時,一棟已建40多年的石頭古厝里,幾名婦女正在一個暗黑的斗室間里拾掇著,這里曾是陳淑榮和黃淑霞的臥室。按照當(dāng)?shù)亓?xí)俗,兩人睡了三四十年的木床拆掉了,椅子、柜子、衣裳都被整理出去。不到6平方米的斗室間,登時開闊了許多。
陳長賢說,“或許這不是偶然,是兩人的心已連在一起了,有了心靈感應(yīng)!”奶奶雖已83歲高齡,但平時身體硬朗,爺爺患病一年來,洗衣、蓋被、燒飯、喂藥都是奶奶做的。
心思專家王永梅認(rèn)同這一說法。她說,相伴相隨多年,會相互牽掛相互需要,一個逝世,另一個會感覺落單了,精力支柱倒了,生存愿望也會隨之不見。
“另一方面,看上去狀況極好的白叟,究竟年紀(jì)大了,身體潛藏著疾病風(fēng)險,一旦遭受老伴逝世,憂傷郁積于心,一口氣喘不過來,適應(yīng)、抗壓才能會下降,身體機能就迅速衰竭了。有時精力沖擊引發(fā)心思潰散,會變成致命一擊。”
王永梅還介紹,相伴多年的老夫妻、深愛的戀人、母子及雙胞胎等,簡單構(gòu)成規(guī)則性行為方法,思想方法附近乃至同步,由此考慮時發(fā)生相似腦電波構(gòu)成磁場,就出現(xiàn)所謂心靈感應(yīng)、第六感。
我們祝愿這對老人,希望他們的愛在天堂里能夠有更美好的延續(xù)。
以上內(nèi)容由www.irislcn.com整理編輯